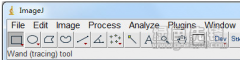|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撰写的《中国人的习惯》一书近日出版,书中认为:中国人养成的习惯是内省,以内省为基底,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推己及人的,社会习惯是和而不同的,生活习惯是择善而从的,工作习惯是勤勉好学的,休闲习惯是张弛有度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邱泽奇带着学生到湖北省麻城县做乡村调查,其中的一项活动是到农户家里做访谈。 邱泽奇记得:“房屋是传统的两三间格局,小青瓦或茅草盖起的人字屋顶,泥土糊的墙壁。房屋里除了吃饭的桌凳,很少有其他家具。家里的大人多数时间在地里劳动,回到家里要么弄口饭吃,要么累极了睡觉。屋子根本没人有时间收拾,哪儿哪儿都是灰尘,餐具也不那么清洁干净。” 生活虽苦,可礼节没有废。大学老师带学生来,主人家尊称其为“先生”并客气让座,“板凳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接着,拿碗从水缸里舀一碗水端上来请老师和学生喝,碗口还留着油渍”。 邱泽奇入乡随俗了。这一场景,可以称之为扎实的学术作风,或者是对对方的体恤体察,当然也是拉近距离的田野调查工作方法,等等。当然,也可以就是简简单单的“入乡随俗”四个字。 后来邱泽奇的学术足迹遍及四大洲,去了北京、新加坡、美国、瑞典和瑞士。他去的地方越多、读的书越多、见的人和事越多,就越是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当年的举动。在《中国人的习惯》里,他意识到,当年在麻城发生的,其实也是一种规则冲突—— “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知道,讲卫生才能保健康。如果老师和学生遵循自己的规则讲卫生,可以先找块抹布把板凳擦干净再坐,找块干净的布或纸把碗口擦干净再喝。可如果老师和学生这么做了,在主人家眼里,老师和学生就成了外人,访谈便再也没法进行,不止这一家,整个村子的访谈都无法继续。这是因为,在乡村社会,没有秘密可言,老师和学生在一家的行为很快会传遍整个村子。如果老师不擦板凳和碗口,直接坐,直接喝,老师便遵循了主人家的社会规则,后面的事情也就顺利了,可这样却违背了老师和学生的社会规则。这个例子便是不同社会规则在具体实践场景里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当然不只是发生在老师带学生进行乡村调查的场景中,在任何一个跨时空的场景中,都潜藏着不同层级的规则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冲突。” 邱泽奇认为,我们是由社会规则冲突塑造的一代人,身上有家乡的社会规则,有游历中国时面对过的社会规则,有游历世界时面对过的社会规则,更有面向未来挑战的有待创新的社会规则。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走出千里万里,语言、风俗、规则、文化的差异更加直接和明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另一方水土里成长的人,自然也养成了他们的习惯,遵循那个环境的社会规则。既然各自有自己的社会规则,便意味着自己的社会规则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更难说是唯一正确的规则。当两种甚至更多规则相遇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对自己的规则是坚守还是放弃?在中国人的习惯里,又如何处理和面对以共识为基础的多种规则差异? 邱泽奇认为,在各种习惯中,最基底、最深层,也最值得讨论的是思维习惯。以“吾日三省吾身”为代表的“内省”,是古代中国人修身和行为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里,修身与内省(自省)是重要的内容。有学者对包含了3461部中华经史子集典籍的语料库进行检索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1089条内容涉及“内省”。其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自察,以他人为镜子自我检查,典型的例子如“见贤思齐”;第二、自讼,自己对照镜子,明确知错后的自我批评、批判。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邱泽奇认为,中国人以自察为基本手段,通过改过、预防、提升来修身,并将内化的善转化为日常实践,在自处、家庭、邻里、朋友、同事、政务活动中予以贯彻。这便是中国文化里的思维习惯,指导着中国人的无意识社会行动,“用当下语言说,中国文化主张自律。在自律中更主张培养随时自我检查的习惯,发现过错并用自我批判进行补救”。 内省不只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当代中国人面对现实社会的思维习惯。在一个倡导为善的社会中,人们会用当下的场景来推演自己在未来场景(如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动)中可能产生的反应,从而决定自己应该如何行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需要的,才可以加诸他人和社会;自己不需要的,不可以加诸他人和社会。在后人的体悟和归纳中,这两条标准被称为处理人己关系的黄金准则,即“推己及人”。就像费孝通先生说的,“一事当前,先想想,这样对人好不好呢?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体会一下心情”。 中国社会的精妙之处在于,中国人有共同的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五彩纷呈的差异风俗之上,更有总体性的社会伦理。 无论是儒墨道法,还是外来的各类宗教,只要在中国的,都贯串了一个基本倾向,那就是以内省为基本形式,以人己关系的情景预见为基本场景,指向社会向善的系统性教化。各地语音不同,行为各异,风俗有别,可贯彻的依然是“仁义礼智信”的中国文化内核。这便是相异中的大同,是从家庭到国家对每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教化。教化塑造了中国人留存至今的思维形式,使得“内省”和“推己及人”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烙印。 读+:正如您在《中国人的习惯》书中所说,关于“习惯”这个话题,每个中国人的日常实践比起学者的理论回应更有意义。您认为“内省”和“推己及人”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习惯,那么在当下的日常实践中,“推己及人”有着怎样的表现? 邱泽奇:推己及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熟人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己及人之所以能发挥效用,成为中国人处理人己关系的黄金准则,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人交往结构的高度稳定性。传统社会的聚居格局、生产方式和交通条件,使得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非常稳定的交往结构中。无论是家族性还是杂居性聚居,无论是村落还是城镇,在相对稳定的交往结构中,相互熟悉的人更容易对彼此形成固定印象,从而获得别人对自己相对稳定的评价。在一个社会向善的整体环境中,他人的评价直接决定了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也决定了自己上升的机会,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家人或家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怎么可能不在意他人的看法呢? 当下的中国要面对个体化社会的崛起,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数字化和全球化这5股力量驱动着社会变革,正在急剧地改变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传统,也在改变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人口很少流动。如今人口流动成为常态,流动人口从最初的几百万到如今的每年4亿人左右,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处在流动中。人口流动给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环境约束消逝了。一个人的周围不再是自己熟悉的人,也不再是熟悉自己的人;自己的行动不再是家庭、邻里、村寨的人评价自己的依据;自己也可以不再考虑对家庭、邻里、村寨的影响。人在流动中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世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人便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且一定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大有不同。 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让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移动终端的普及几乎让每一个人都卷入了在线社交网络。后果是,每一个人都处于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场景中,即使是身边的人,也有可能与自己三观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们抱怨孩子越来越难管,父母越来越难伺候,配偶越来越难沟通。基于家庭、社区、人群的“礼”,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 工业化给个体提供工作,市场化给个体提供生活,城镇化为个体提供独立空间,数字化让个体连接到任何“人”,全球化则把个体带到任何“己”想去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社会,“己”被局限在自己出生的步行范围内;如今,这个范围被扩大到了整个地球。“己”可以不再适应“人”,而是去满世界寻找可以匹配“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变化、革命性的变化。这个社会的崛起,是一种世界潮流,如今中国人也加入其中。 简而言之,推己及人是以整个社会共有价值观为基础、以村社乡里等地方性共同体为范围,把个体放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思维方式。推己及人的底线是整个社会共有的价值观,这一点仍旧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读+:您曾经两次前往非洲研究过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取得了若干学术成果。能否说说,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给中国人“走世界”带来哪些优势? 邱泽奇:尊重他人,并且尊重他人的规则,这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也是习惯。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入乡随俗”。 以中国援非为例,中国人不把援助作为强制力量,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强迫非洲人接受外来文化;而是把援助作为伴手礼,表达我们对非洲的善意,譬如,先给人治病,帮人建医院,与非洲人交朋友。先交朋友再说其他,“朋友在先”,这是中国人在外做事的方式。 “应需而援”就是尊重非洲国家的体现,考虑对方的需要,不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他人。中国人的这些文化习惯,至少为他人尊重自己提供了前提,也因此占据了道德优势;还为理解他人提供了契机,尊重他人便是理解他人的入口。 在中国医疗队驻地,我们了解到,中国大夫用自己的行动,获得了当地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认同。在他们眼中,中国医疗队确实是来帮助当地患者的;他们专业技术水平高超、对患者亲切体贴、对自己严格要求,让“主人”体会到“客人””的一片真诚。来自客人的真诚,破解了主客之间的隔阂,让主客之间产生了沟通的期待与意愿。 读+:您在书中归纳了中国人的几种习惯,这些习惯是中国人独有的吗?比如,“勤勉好学的工作习惯”“张弛有度的休闲习惯”,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就没有这些习惯吗? 邱泽奇:有些习惯或许不是中国人独有,可是其文化逻辑却是中国人独有的。就拿“勤勉好学”的工作习惯来说,在中国人的文化逻辑里,“勤勉好学”与“内省”的基底相关联,与“将勤补拙”“见贤思齐”相表里,自然、顺畅,没有一点违和感,也不需要解释;可是,在西方人的工作习惯里,这却需要解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不得不用“天职观”来解释。不仅工作习惯如此,中国人的每一个底层习惯,都可以从“内省”中衍生出来。 读+:中国人的习惯已经走过了千百年,您能否预测一下,会有哪些习惯发生变化,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习惯? 邱泽奇:习惯是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是在变化之中的,有一些习惯会变,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不过,文化是有结构的,也是有层次的。一些习惯可能还会保留相当长的时间,譬如“内省”。一些习惯则会随场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自然也会形成一些新的习惯,譬如,在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人就不大会呈现自己,学会“呈现”,自然会形成一些新的前端的习惯。需要强调的是,一个人肉身具在的物理空间是有限的,人生活的空间,通常是肉身具在的物理空间,仍然是一个相对而言的熟人社会。因此,新形成的习惯,依然不可能是主流的习惯,而只是能够理解其他文化的、美人之美的习惯而已。 只要中国人的教育结构还在、只要家庭还是中国人固守的归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就会延续,后端习惯就会坚守。 我们是由历史巨变塑造的一代人,身上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革命精神的种子,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更有面向未来挑战的文化使命。 无论如何,当下的困境也许只是历史上众多困境中的一个段落而已。中国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分分合合,也经历过无数回试图改变中国文化基因的冲击。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的确与前一个时代有差别,形式有变化、方法有改进,可本质依旧在延续。我们中国人,对人性的基本认识依旧是多元的,处理人己关系的思维还是推己及人,对差异的包容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依旧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寻找榜样而不是敌人,依旧把勤勉努力作为达成目标的基本路径,依旧在克制地对待人性中不受社会欢迎的部分。中国文化原本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诸子百家不过是多元思想和观点的呈现而已。中国文化在面对更加多元的文化时,不仅有足够的资源,也有足够的容量见贤思齐,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从而变得更加丰富,也让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多元,让中国人对不同行为习惯的理解更加自觉。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撰写的《中国人的习惯》一书近日出版,书中认为:中国人养成的习惯是内省,以内省为基底,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推己及人的,社会习惯是和而不同的,生活习惯是择善而从的,工作习惯是勤勉好学的,休闲习惯是张弛有度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邱泽奇带着学生到湖北省麻城县做乡村调查,其中的一项活动是到农户家里做访谈。 邱泽奇记得:“房屋是传统的两三间格局,小青瓦或茅草盖起的人字屋顶,泥土糊的墙壁。房屋里除了吃饭的桌凳,很少有其他家具。家里的大人多数时间在地里劳动,回到家里要么弄口饭吃,要么累极了睡觉。屋子根本没人有时间收拾,哪儿哪儿都是灰尘,餐具也不那么清洁干净。” 生活虽苦,可礼节没有废。大学老师带学生来,主人家尊称其为“先生”并客气让座,“板凳上积着厚厚的灰尘。接着,拿碗从水缸里舀一碗水端上来请老师和学生喝,碗口还留着油渍”。 邱泽奇入乡随俗了。这一场景,可以称之为扎实的学术作风,或者是对对方的体恤体察,当然也是拉近距离的田野调查工作方法,等等。当然,也可以就是简简单单的“入乡随俗”四个字。 后来邱泽奇的学术足迹遍及四大洲,去了北京、新加坡、美国、瑞典和瑞士。他去的地方越多、读的书越多、见的人和事越多,就越是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当年的举动。在《中国人的习惯》里,他意识到,当年在麻城发生的,其实也是一种规则冲突—— “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知道,讲卫生才能保健康。如果老师和学生遵循自己的规则讲卫生,可以先找块抹布把板凳擦干净再坐,找块干净的布或纸把碗口擦干净再喝。可如果老师和学生这么做了,在主人家眼里,老师和学生就成了外人,访谈便再也没法进行,不止这一家,整个村子的访谈都无法继续。这是因为,在乡村社会,没有秘密可言,老师和学生在一家的行为很快会传遍整个村子。如果老师不擦板凳和碗口,直接坐,直接喝,老师便遵循了主人家的社会规则,后面的事情也就顺利了,可这样却违背了老师和学生的社会规则。这个例子便是不同社会规则在具体实践场景里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当然不只是发生在老师带学生进行乡村调查的场景中,在任何一个跨时空的场景中,都潜藏着不同层级的规则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冲突。” 邱泽奇认为,我们是由社会规则冲突塑造的一代人,身上有家乡的社会规则,有游历中国时面对过的社会规则,有游历世界时面对过的社会规则,更有面向未来挑战的有待创新的社会规则。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走出千里万里,语言、风俗、规则、文化的差异更加直接和明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另一方水土里成长的人,自然也养成了他们的习惯,遵循那个环境的社会规则。既然各自有自己的社会规则,便意味着自己的社会规则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更难说是唯一正确的规则。当两种甚至更多规则相遇时,我们该如何面对?对自己的规则是坚守还是放弃?在中国人的习惯里,又如何处理和面对以共识为基础的多种规则差异? 邱泽奇认为,在各种习惯中,最基底、最深层,也最值得讨论的是思维习惯。以“吾日三省吾身”为代表的“内省”,是古代中国人修身和行为的基本方式,也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在中国的文化典籍里,修身与内省(自省)是重要的内容。有学者对包含了3461部中华经史子集典籍的语料库进行检索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有1089条内容涉及“内省”。其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自察,以他人为镜子自我检查,典型的例子如“见贤思齐”;第二、自讼,自己对照镜子,明确知错后的自我批评、批判。 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分析,邱泽奇认为,中国人以自察为基本手段,通过改过、预防、提升来修身,并将内化的善转化为日常实践,在自处、家庭、邻里、朋友、同事、政务活动中予以贯彻。这便是中国文化里的思维习惯,指导着中国人的无意识社会行动,“用当下语言说,中国文化主张自律。在自律中更主张培养随时自我检查的习惯,发现过错并用自我批判进行补救”。 内省不只存在于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当代中国人面对现实社会的思维习惯。在一个倡导为善的社会中,人们会用当下的场景来推演自己在未来场景(如他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动)中可能产生的反应,从而决定自己应该如何行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需要的,才可以加诸他人和社会;自己不需要的,不可以加诸他人和社会。在后人的体悟和归纳中,这两条标准被称为处理人己关系的黄金准则,即“推己及人”。就像费孝通先生说的,“一事当前,先想想,这样对人好不好呢?那就先假定放在自己身上,体会一下心情”。 中国社会的精妙之处在于,中国人有共同的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在五彩纷呈的差异风俗之上,更有总体性的社会伦理。 无论是儒墨道法,还是外来的各类宗教,只要在中国的,都贯串了一个基本倾向,那就是以内省为基本形式,以人己关系的情景预见为基本场景,指向社会向善的系统性教化。各地语音不同,行为各异,风俗有别,可贯彻的依然是“仁义礼智信”的中国文化内核。这便是相异中的大同,是从家庭到国家对每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教化。教化塑造了中国人留存至今的思维形式,使得“内省”和“推己及人”成为中国人的思维烙印。 读+:正如您在《中国人的习惯》书中所说,关于“习惯”这个话题,每个中国人的日常实践比起学者的理论回应更有意义。您认为“内省”和“推己及人”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习惯,那么在当下的日常实践中,“推己及人”有着怎样的表现? 邱泽奇:推己及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熟人社会。在传统中国社会,推己及人之所以能发挥效用,成为中国人处理人己关系的黄金准则,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人交往结构的高度稳定性。传统社会的聚居格局、生产方式和交通条件,使得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关系非常稳定的交往结构中。无论是家族性还是杂居性聚居,无论是村落还是城镇,在相对稳定的交往结构中,相互熟悉的人更容易对彼此形成固定印象,从而获得别人对自己相对稳定的评价。在一个社会向善的整体环境中,他人的评价直接决定了自己的地位和声望,也决定了自己上升的机会,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家人或家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人怎么可能不在意他人的看法呢? 当下的中国要面对个体化社会的崛起,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数字化和全球化这5股力量驱动着社会变革,正在急剧地改变中国绵延了几千年的传统,也在改变中国人传承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人口很少流动。如今人口流动成为常态,流动人口从最初的几百万到如今的每年4亿人左右,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处在流动中。人口流动给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环境约束消逝了。一个人的周围不再是自己熟悉的人,也不再是熟悉自己的人;自己的行动不再是家庭、邻里、村寨的人评价自己的依据;自己也可以不再考虑对家庭、邻里、村寨的影响。人在流动中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进入了一个更为自由的世界。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人便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且一定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大有不同。 数字技术的社会化应用让人们的社会交往范围进一步扩大。移动终端的普及几乎让每一个人都卷入了在线社交网络。后果是,每一个人都处于高度异质化的社会场景中,即使是身边的人,也有可能与自己三观不同。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们抱怨孩子越来越难管,父母越来越难伺候,配偶越来越难沟通。基于家庭、社区、人群的“礼”,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 工业化给个体提供工作,市场化给个体提供生活,城镇化为个体提供独立空间,数字化让个体连接到任何“人”,全球化则把个体带到任何“己”想去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社会,“己”被局限在自己出生的步行范围内;如今,这个范围被扩大到了整个地球。“己”可以不再适应“人”,而是去满世界寻找可以匹配“己”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变化、革命性的变化。这个社会的崛起,是一种世界潮流,如今中国人也加入其中。 简而言之,推己及人是以整个社会共有价值观为基础、以村社乡里等地方性共同体为范围,把个体放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的思维方式。推己及人的底线是整个社会共有的价值观,这一点仍旧扎根在每一个人的心里。 读+:您曾经两次前往非洲研究过中国对乌干达的卫生发展援助,取得了若干学术成果。能否说说,中国人的文化习惯给中国人“走世界”带来哪些优势? 邱泽奇:尊重他人,并且尊重他人的规则,这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也是习惯。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入乡随俗”。 以中国援非为例,中国人不把援助作为强制力量,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强迫非洲人接受外来文化;而是把援助作为伴手礼,表达我们对非洲的善意,譬如,先给人治病,帮人建医院,与非洲人交朋友。先交朋友再说其他,“朋友在先”,这是中国人在外做事的方式。 “应需而援”就是尊重非洲国家的体现,考虑对方的需要,不把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他人。中国人的这些文化习惯,至少为他人尊重自己提供了前提,也因此占据了道德优势;还为理解他人提供了契机,尊重他人便是理解他人的入口。 在中国医疗队驻地,我们了解到,中国大夫用自己的行动,获得了当地医院医护人员和患者的认同。在他们眼中,中国医疗队确实是来帮助当地患者的;他们专业技术水平高超、对患者亲切体贴、对自己严格要求,让“主人”体会到“客人””的一片真诚。来自客人的真诚,破解了主客之间的隔阂,让主客之间产生了沟通的期待与意愿。 读+:您在书中归纳了中国人的几种习惯,这些习惯是中国人独有的吗?比如,“勤勉好学的工作习惯”“张弛有度的休闲习惯”,世界上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就没有这些习惯吗? 邱泽奇:有些习惯或许不是中国人独有,可是其文化逻辑却是中国人独有的。就拿“勤勉好学”的工作习惯来说,在中国人的文化逻辑里,“勤勉好学”与“内省”的基底相关联,与“将勤补拙”“见贤思齐”相表里,自然、顺畅,没有一点违和感,也不需要解释;可是,在西方人的工作习惯里,这却需要解释。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不得不用“天职观”来解释。不仅工作习惯如此,中国人的每一个底层习惯,都可以从“内省”中衍生出来。 读+:中国人的习惯已经走过了千百年,您能否预测一下,会有哪些习惯发生变化,会不会出现一些新的习惯? 邱泽奇:习惯是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是在变化之中的,有一些习惯会变,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不过,文化是有结构的,也是有层次的。一些习惯可能还会保留相当长的时间,譬如“内省”。一些习惯则会随场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自然也会形成一些新的习惯,譬如,在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人就不大会呈现自己,学会“呈现”,自然会形成一些新的前端的习惯。需要强调的是,一个人肉身具在的物理空间是有限的,人生活的空间,通常是肉身具在的物理空间,仍然是一个相对而言的熟人社会。因此,新形成的习惯,依然不可能是主流的习惯,而只是能够理解其他文化的、美人之美的习惯而已。 只要中国人的教育结构还在、只要家庭还是中国人固守的归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就会延续,后端习惯就会坚守。 我们是由历史巨变塑造的一代人,身上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有革命精神的种子,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更有面向未来挑战的文化使命。 无论如何,当下的困境也许只是历史上众多困境中的一个段落而已。中国曾经经历过无数次的分分合合,也经历过无数回试图改变中国文化基因的冲击。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的确与前一个时代有差别,形式有变化、方法有改进,可本质依旧在延续。我们中国人,对人性的基本认识依旧是多元的,处理人己关系的思维还是推己及人,对差异的包容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依旧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寻找榜样而不是敌人,依旧把勤勉努力作为达成目标的基本路径,依旧在克制地对待人性中不受社会欢迎的部分。中国文化原本就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诸子百家不过是多元思想和观点的呈现而已。中国文化在面对更加多元的文化时,不仅有足够的资源,也有足够的容量见贤思齐,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从而变得更加丰富,也让中国人对人性的认识更加多元,让中国人对不同行为习惯的理解更加自觉。 |
热门关键词: